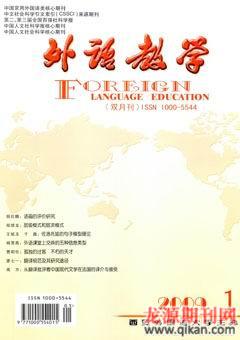詞典與外語教學學理界面研究
陳 偉
摘 要:詞匯是語言的中心,詞匯能力則是語言能力的基礎,因此詞匯教學歷來是外語教學的核心任務;詞典的基本處理單元是語言中的詞匯,它以描寫自然語言中詞匯的信息為己任?本文以詞典教學功能為運思切入點并立足理論研究系統(tǒng),分別從意義哲學(本體論)?二語習得屬性(認識論)與教學機制(方法論)三個層面對詞典與外語教學對接界面的學理歸因進行了研究,以期廓清兩者積極互動的理論視域?
關(guān)鍵詞:詞典;外語教學;意義哲學;二語習得;教學機制
中圖分類號:H3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544(2009)01-0063-07
Abstract:Dictionary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re interrelated since the former aims at describing the lexical information of words while the latter embraces the key task of vocabulary teaching. Based on the didactic function of dictionary paradigm, the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interface between dictionary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philosophy of meaning, L2 acquisition and teaching mechanism.
Key words: dictionar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hilosophy of meaning; L2 acquisition; teaching mechanism
1.引言
通常說來,語言具有三大要素:語音?詞匯和語法?后兩者構(gòu)成了語言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詞匯是基本構(gòu)件,語法則是將這些構(gòu)件組合起來的粘合劑?語言詞匯論者認為,“語言是語法化的詞匯,而不是詞匯化的語法”(Lewis 1993),可見,詞匯是語言的中心,對學習者來說至關(guān)重要(Zimmerman 1997),正如Wilkins(1972: 111)所說:“沒有語法而能傳遞的東西很少,沒有詞匯則什么東西也無法傳遞?”在詞匯論者看來,詞庫是語義和句法信息的主要來源,所有語法特征都附著于詞匯;從詞匯入手同樣可以探求語法機制,甚至更方便?更直接——因為“詞匯是最精密的語法”(Halliday 1961)?從語言能力角度來說,詞匯能力是語言能力的基礎,因而詞匯在語言習得和使用中占據(jù)了中心地位(Coady & Huckin 1997),詞匯教學也因此成為外語教學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與核心組成部分(Allen 1983; Harley 1995; Schmitt & McCarthy 1997)?Widdowson(1992)更是指出,外語教學其“直接目的就是發(fā)展學習者的二語詞匯能力”?縱觀外語教學史,詞匯教學基本上算是歷來受到重視?20世紀初期,無論是H. E. Palmer在日本推行口語教學法,還是M. P. West在印度倡導閱讀教學法,都以詞匯為基礎的?只是其后到60年代,在N. Chomsky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思想流溢所形成的張力下,外語教學一度強調(diào)句法的作用?但是最近20多年,外語教學中詞匯論重新興起,語言解釋的焦點從語言結(jié)構(gòu)的事實回歸詞匯的事實,語言描寫的重點也由“以語法規(guī)則為中心”轉(zhuǎn)移到“以詞庫為中心”?
詞典是人類文明的產(chǎn)物?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產(chǎn)品,詞典的基本處理單元就是語言中的詞匯,它以描寫自然語言中詞匯的信息為己任,一切工作都圍繞著詞匯而展開?具體地,詞典就是通過提供詞匯的各種實用“語義信息”,以滿足使用者在語言學習或使用中的詞匯信息需求,從而完成“解惑釋疑”的使命?正是以“詞匯”為接口,近年來外語教學共同體越來越重視詞典對于外語教學的重要影響與作用,不但增強了對各個類別或?qū)哟瓮庹Z學習者詞典使用策略的調(diào)查與研究力度,而且很多高校語言學系?外語系都積極開設詞典課程,并從教學方法?教材建設等方面進行系統(tǒng)規(guī)劃?有的高校甚至已經(jīng)將詞典課程建設成為英語系的專業(yè)強項,從而形成了自己的英語專業(yè)特色及新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陳偉(2008)立足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及其思想特征,就語言教育共同體內(nèi)涌現(xiàn)的這一潮流所蘊涵的后現(xiàn)代教育理念?內(nèi)涵及其意義進行了挖掘與解讀?他認為,詞典課程開設切合當前以知識經(jīng)濟全球化為特征的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是課程與教學改革基于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可行選擇與建構(gòu);對于它的研究,能夠為課程與教育學科改革及現(xiàn)代化發(fā)展提供創(chuàng)新理路?本文要研究的問題是:詞典與外語教學對接的界面有著怎樣的學理歸因?這一問題的解決期望能夠廓清兩者積極互動的理論視域,從而指明兩者構(gòu)建“機理相通?效用交錯”的科學路向?
2.詞典與教學功能
詞典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從來不是鄉(xiāng)野中自生自滅的天然花草;它的發(fā)軔?存在和發(fā)展與社會進化?國際關(guān)系的發(fā)展及各種非語言因素直接相關(guān),因而總是承載著特定的社會任務與社會功能?加克(1981)將詞典功能概括為四類:不同語言間的交際;語言教學,解釋難懂的詞;描寫國語并使之規(guī)范化;對語言的科學研究?雍和明(2003: 4)則綜合其他詞典學家的觀點,將詞典功能歸納為三種:描寫功能?教導功能(didactic function)與意識功能?可見,教學功能是詞典范式(或產(chǎn)品)的重要功能,就社會使用而言,也無疑是詞典功能中最為根本的:它提供關(guān)于語詞的意義和用法指南,從而發(fā)揮著典范性的教導作用,并最終改善?提高文化內(nèi)與文化間語言交際的質(zhì)量和水平?
加克(1981)對詞典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進行了研究,他指出,“詞典史向我們揭示出,其產(chǎn)生伊始就有教育方面的任務:講解令人不甚了解的詞語,教授青年一代(成年人也包括在內(nèi))文明語言?”剖析詞典史不難發(fā)現(xiàn),成形詞典產(chǎn)生以前的辭書以及第一批詞典,主要就是教學詞典和教學材料?以16世紀處于黎明時期的歐洲詞典為例,第一部用該國語言編寫的詞典都是供教學使用的,如第一部拉丁語-英語詞典《兒童詞庫》?法語-拉丁語詞典《青年詞書》?波蘭語-拉丁語-立陶宛語詞典《青年學生三種語詞典》等?加克總結(jié)認為,“任何一部詞典,首先都有教學論方面的意義,也就是說,它是供教學使用的著作?”杰尼索夫(1981)對各國詞典學歷史過程進行分析后指出,對“正在成長的一代進行教育的實際需要”是詞典產(chǎn)生與發(fā)展的關(guān)鍵因素,“教育”作用位居語言描寫(詞典和語法)的普遍作用之首?
詞典的教學功能不僅體現(xiàn)在單語詞典類型上,雙語詞典更是作為外語教學的一種重要工具而出現(xiàn)的?黃建華等(2001: 10)研究指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早期的雙語詞典已負有教學方面的任務,也就是說大都以供學習者使用為宗旨?”研究表明,雙語詞典早在15世紀就與語言教學緊密相聯(lián)?雙語詞典責無旁貸地以外語學習者從語言能力?文化能力到社交能力的成熟為己任,為外語學習者發(fā)揮著典范的教導作用?詞典教學功能的增強與完善甚而催生了教學詞典學,加克(1981)指出,從應用語言學角度來看,教學詞典學在詞典學中即使不是最古老的,也是頗為古老的一個學科?
列寧一直強調(diào)詞典在教學論方面的作用,他(轉(zhuǎn)自加克 1981)認為,詞典不僅是一本查考資料的參考書,更是一種有助于人們接受教育并促使其語言形成的工具書?詞典范式(或產(chǎn)品)以教學功能為本,縱觀詞典范式演變史,教育教學領域的理論及其變革也深刻影響著詞典業(yè)的發(fā)展與走向?當代詞典文本更是將教學特性張揚到極致,一方面積極對語言教學語境進行模擬,以期最佳地迎合語言教學規(guī)律而實現(xiàn)最優(yōu)的詞典教學效果,另一方面采取科學編纂手段,在詞典微觀與宏觀結(jié)構(gòu)中有效復制外語教學與習得的特點和規(guī)律,旨在真正實現(xiàn)詞典作為語言教學橋梁的價值(陳偉,等 2007)?立足學術(shù)研究系統(tǒng)進行考察不難發(fā)現(xiàn),詞典與外語教學的對接界面也具有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層面的學理特征或歸因,具體分別體現(xiàn)為意義哲學?二語習得屬性與教學機制?
3.意義哲學本體論:意義的追蹤與建構(gòu)
人與其他動物的最大差別可能就在于:人在與外物接觸過程中,總是把自己的思想內(nèi)涵像標簽一樣賦予外物,從而使得這些外物具有了相應意義?這一標簽式意義說明,人是生活在一個意義的世界中,意義是人類所特有的?人正是通過對事物和世界意義的理解來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的,同時意義也體現(xiàn)出人與社會?自然?他人?自己的種種錯綜復雜的文化關(guān)系?歷史關(guān)系?心理關(guān)系和實踐關(guān)系?事實上,意義是人類最基本的活動之一,人在充滿意義的世界中從事各種社會實踐,以有意義的物質(zhì)為實踐客體,又以追求甚至創(chuàng)造意義為終極目標?智慧?賢明的人類正是在后天文化環(huán)境中通過意義的引導和注入,最終體現(xiàn)出人的主體性特征,并把研究整個世界一般規(guī)律的根本觀點的學問——哲學——的中心問題定位在了意義角度,而對語義來源?生成和使用特征的追尋則成了“我們把握當代諸多哲學和文化思潮的有效路徑”(徐海銘,等 2005)?
語言是人類所特有的,人類語言交際所依賴的語言符號(系統(tǒng))并非一種空洞的物理形式,同樣“是人類的意義世界之一部分”(卡西爾 1985: 41),即意義的載體?F. De Saussure所說“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tǒng)”,其“觀念”實際上就是指語言符號所具有的意義?沒有意義的語言符號不能稱之為符號?作為人類歷史上古老的一種文化產(chǎn)品,詞典本質(zhì)上就是語言的詞典,是存在于人類之外的三種語言模式之一,它“匯集語言里的詞語,按一定方式編排,逐條加以釋義或提供有關(guān)信息”?
意義問題正是詞典編纂的核心問題?這秉承了人與語言的意義特性?Béjoint(1981)指出,“查閱意義似乎是詞典使用最普遍動機”?研究人員調(diào)查表明,學習者使用詞典主要就是查詢意義?例如,Tomaszczyk(1979)針對以英語作為外語的學習者進行研究后發(fā)現(xiàn),語文詳解詞典首先就是被用于查詢意義(定義或?qū)Φ仍~)?Iannucci(1976: 1)則研究指出,“詞典,無論是單語還是雙語的,從根本上來說都是處理意義的工具”?總之,用戶的詞典查詢過程就是意義的追蹤?認定與構(gòu)建過程,這既包括用戶自然能動地參與到詞典文本的符碼意指和意義生成中,也包括詞典文本系統(tǒng)自身的意義呈顯與智力引發(fā)?
“詞典學理論涉及到對語言最復雜的一個平面的描寫,即描寫的是和使用該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和文化有密切聯(lián)系的語義平面?”(杰尼索夫 1981)基于詞典的意義特性,對語詞不同類型的意義進行闡釋(建構(gòu)語言的“詞匯?語義”系統(tǒng))就成了詞典編纂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事實上,詞典的一切工作都是圍繞著釋義而展開?Nida(1964: 121)指出,“語義學所研究?調(diào)查的主要思想都體現(xiàn)在詞典編纂上”?現(xiàn)代詞典積極運用語義結(jié)構(gòu)?認知概念結(jié)構(gòu)?語義分解理論?語義場理論?原型理論?配價理論?語用學原理等意義理論進行釋義,以多維度?多視角地揭示和表述語詞的意義,反映意義的多維表象?
外語教學本質(zhì)上也是一種面向意義的活動?桂詩春(2005)從交際目的?教學中心向詞匯轉(zhuǎn)移和以語言形式為焦點的角度進行研究后指出,“外語教學的根本目的就是教會學習者用外語來表達他們心中的意義”?他認為,母語習得是和意義連在一起的,母語對學習外語所起的遷移作用,實際上就源于我們要用另一種語言來表達我們用母語所表達的意義?言語失誤方面的研究表明,外語學習者在學習一種新的語言形式時習慣于賦予它某種(詞匯的或語法的)意義,因為沒有掌握合適的英語表達方式去表達相應漢語意思,這時往往出現(xiàn)語言遷移?因此,外語教學活動實際上就是一種意義使用行為,而這后者“從本質(zhì)上闡明了語言習得的特性”(徐海銘等 2005)?如果說兒童在早期主要是通過模仿?操練以及記憶來習得詞語意義的話,那么到后來他們主要就是通過理解自然輸入?吸收語言規(guī)則及語言使用的社會規(guī)約來習得意義的?這決定了:外語教學是意義習得必不可缺的過程?桂詩春說:“面向意義體現(xiàn)了一種教學重心向詞匯的轉(zhuǎn)變?”詞典與外語教學在詞匯層面的對接是人的主體性的自然表征,體現(xiàn)出意義哲學探求人性中心與知識本原沖動的張力效應?
4.二語習得屬性認識論:效應的可行與可及
Lewis(1993)說:“所有自然語言的使用,不管是接受性的,還是產(chǎn)出性的,都建筑在與認知有關(guān)的過程中?”這說明,語言是以認知為基礎的?詞典與外語教學處理的都是自然語言,因而本質(zhì)上都是一個認知過程,都以認知為基礎,只不過就教學特性而言,前者是隱性的,后者是顯性的?因此,強調(diào)詞典與外語教學的對接,我們無法回避二語習得視角的學理屬性:它立足外語教學的過程?感知?記憶?問題求解以及決策,探討學習者為了促進語言學習所采取的系列學習策略,以解釋語言中的詞匯—語義鏈和詞義習得機制?探求這一層面的理論歸因,實際上反映出人們對于兩者認知對接的認識論追求及層次?
4.1 詞典與詞匯學習策略
學習策略是指學習者為了能夠更好地理解?學習或記憶新信息而運用的有目的的行為與思維;學習策略直接影響到語言學習的有效性?OMalley & Chamot(1990)將詞匯學習策略分為兩個層次:元認知策略與認知策略?認知策略是學習者對學習材料的應對和學習中所出現(xiàn)的問題的解決,其中就包括詞典使用策略?Ahmed(1989)調(diào)查了蘇丹首都喀土穆的英語學習者后發(fā)現(xiàn),盡管不同水平層次的學習者查詢詞典的場合與方式不一樣,但詞典使用確實有著積極意義?他同時發(fā)現(xiàn),善于使用學習策略的人,也善于使用詞典;幾乎不用任何學習策略的人,也一般不查詞典?這一結(jié)論得到了Politzer & McGroarty(1985),Porte(1988)等研究者的支持?
4.2 詞典使用:詞匯學習的直接法還是伴隨法
詞匯學習大體上分為兩大類方法:直接法與伴隨法?根據(jù)Nation(1990),直接法是指學習者做一些能將注意力集中在詞匯上的活動或練習,而伴隨法則是指學習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其它方面,尤其是語言所傳遞的信息上,而不需要對詞匯進行專門學習便可習得詞匯?那么,詞典使用是詞匯學習的直接法還是伴隨法呢?學術(shù)界對此有著完全相反的兩種觀點?Nation(1990),Ellis(1997),Nagy(1997)等認為,查詢詞典與做各種詞匯練習一樣,是一種有意識的詞匯學習策略,理應歸結(jié)為直接法?Hulstijn則提出了不同觀點,他(1992)將影響詞匯伴隨學習的因素總結(jié)為:1)對新詞匯語義的拓展深度;2)對新詞匯注意力的多少;3)讀者詞匯能力的高低;4)詞典的運用;5)新詞匯旁注的提供;6)單詞的頻率?可見,Hulstijn(1992, 1997)是將詞典使用歸結(jié)為一種伴隨法?他的觀點得到了Nagy,Herman & Anderson(1985)的支持?我們認為,判斷詞典使用屬于直接法還是伴隨法應該取決于學習者的使用目的?使用情境與使用效果?但毋庸置疑的是,詞典使用確實是一種不可忽視?值得深入研究的詞匯認知學習策略?
4.3 詞典使用對于外語學習的積極作用
首先,有助于自主的詞匯學習?這是詞典最為根本的價值:通過使用詞典,學習者可以獨立自主地進行詞匯學習?Allen(1983)探討了非母語英語課程中詞匯教學的技巧問題?他認為,高級詞匯教學階段的重點是培養(yǎng)學生獨立學習詞匯的能力,而“詞典因此變得尤為重要”,所以他指出,“必須首先教會高級學習者好好使用詞典”Grabe & Stoller(1997)?也研究指出,系統(tǒng)?得當?shù)厥褂秒p語詞典對詞匯學習有著積極意義,大量使用詞典能夠使學習者在較短的時間內(nèi)了解?掌握新單詞?
其次,有助于滿足詞匯學習的精確性要求?Grabe & Stoller(1997)進行了一項為期5個月的個案研究,考察學習者在只查閱雙語詞典而沒有任何其它指導的條件下的報紙閱讀效果?結(jié)果發(fā)現(xiàn),詞典使用對于閱讀特別有用,因為詞典從思想上給學習者以有價值的“精確定位”(accuracy anchor),而且增強了繼續(xù)閱讀的信心?這與Luppescu & Day(1993)所得出的“雙語詞典對詞匯習得有著潛在影響”的結(jié)論類似:詞典確實有助于詞匯的習得,盡管使用詞典降低了閱讀速度……對成年學習者來說,準確知道一個詞的意義有時非常重要,詞典正好提供了這一“精確性支持”(accuracy support)?
第三,有助于提高詞匯學習的質(zhì)量?Nation(1990)?Laufer(1998)等認為,詞匯的發(fā)展不只是一個數(shù)量問題,還包括深化詞匯知識深度或質(zhì)量的問題;習得詞匯知識不只是熟悉詞形與標記,還要熟悉各種意義?句法特征?語義特征?組合關(guān)系等?吳霞,等(1998)的研究證明,查詞典對掌握詞匯知識的質(zhì)有較大幫助:詞典不但提供語詞的全面信息,如發(fā)音?用法?意義等,而且通過例證提供語詞的典型用法;學習者可以從詞典中得到關(guān)于語詞的精煉?準確的理解?Stahl & Fairbanks(1986)分析了大約70個有關(guān)詞匯學習指導的研究調(diào)查后發(fā)現(xiàn),對L2學習者來說,提供詳細的釋義與語境信息對詞匯教學的質(zhì)很有效果,而詞典正好具備了這樣的條件?Parry(1991),Luppescu & Day(1993)等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觀點?董燕萍(2001)通過實驗研究增加詞典查詢對交際教學法的影響,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在交際教學法直接學習的基礎上增加詞典查詢有助于學習者的詞匯產(chǎn)出能力?
第四,有助于增強學習者對詞匯的記憶?研究界普遍認為,除了能夠幫助獲取準確信息外,信息加工(如閱讀?寫作等)過程中的詞典使用還有助于強化記憶(Scholfield 1997)?Bogaards(1991)的研究進一步發(fā)現(xiàn),學習者使用單語詞典比使用雙語詞典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加工深度比后者大,因而更有助于記憶?有些研究者(Pressley et al 1982; Cohen 1990; Ellis 1997; Schmitt & McCarthy 1997)還利用二語詞匯研究成果,證明了在學習詞典中使用插圖?真人發(fā)音的例證?關(guān)鍵詞等特殊詞匯記憶策略,同樣有助于增強使用者對詞匯的記憶?有些研究成果已經(jīng)被一些電子詞典加以利用?
當然,要充分實現(xiàn)詞典使用對于外語學習的積極效果,不能回避詞典使用策略問題?詞典使用是一個復雜的認知心理過程,使用者在詞典查詢時表現(xiàn)出不同的方法?目的?偏好與習慣,因而教給他們適當?shù)脑~典使用策略,有助于他們獲得更好的外語學習效果?董燕萍(2001)對大學英語專業(yè)一年級學生的實驗結(jié)果說明,學生大都缺乏基本的詞典使用策略?Oxford & Scarcella(1994)研究指出,對詞匯學習而言,教給學生一些明示策略(explicit strategies)至關(guān)重要,這其中就包括詞典使用策略?Luppescu & Day(1993)針對293名日本大學生的研究證明,詞典使用在提高學生詞匯學習效果的同時,也會造成一定困惑,因此學習者需要接受詞典使用策略的培訓?Scholfield(1997)的研究也肯定了詞典使用這一學習策略的積極效應,他同時呼吁,“為了獲得有效的學習,學習者需要提高詞典使用技能,不能讓這方面的策略能力‘僵化(fossilize)”?
4.4 詞典在不同外語教學任務中的效用
研究人員(Tomaszczyk 1979; Hartmann 1983; Atkins & Varantola 1997)發(fā)現(xiàn),英語學習者使用詞典涉及聽?說?讀?寫等不同學習活動,但主要用于讀?寫等書面語活動,而很少用于說與聽?例如Béjoint(1981)研究指出,學習者主要在解碼型語言活動中使用詞典,具體排序是:翻譯(外語翻譯為母語)?閱讀?寫作?翻譯(母語翻譯為外語)等?在不同外語教學任務中,詞典使用有著不同的效用?
1)詞典與翻譯
詞典對于翻譯的作用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查詢生詞,那么生詞的翻譯質(zhì)量理應比查詢了詞典的翻譯質(zhì)量更差?這一觀點為很多研究結(jié)果所證實?例如Krings(1986)運用有聲思維方法,對德國大學高年級法語學生在翻譯實踐過程中的詞典使用情況進行研究后發(fā)現(xiàn),是否利用雙語詞典直接影響到翻譯質(zhì)量?Li(1998)對中國學生在英漢翻譯過程中的詞典使用進行研究后發(fā)現(xiàn),73%的查詢是成功的,使用詞典確實有助于準確地進行翻譯?當然,詞典使用并非高質(zhì)量翻譯的必要條件,還牽涉到詞典使用策略等關(guān)鍵因素?
2)詞典與閱讀
閱讀是詞典使用的主要領域?一般認為,詞典使用有助于理解閱讀材料內(nèi)容(Tono 1989)?Summers(1998)的研究也證明,在閱讀過程中使用詞典的學生比不使用詞典的學生能更好地理解材料中的語詞?但是,更多研究人員并不支持詞典對于閱讀的正面效應觀,他們或者認為兩者并沒有明顯影響(Bensoussan et al 1984; Nesi & Meara 1994),或者發(fā)現(xiàn)詞典甚至會在閱讀中產(chǎn)生負面效應(Padron & Waxman 1988),或者指出閱讀中使用詞典只能破壞閱讀過程的流暢性(Hosenfeld 1977)?我們認為,接受型詞匯策略研究關(guān)注學習者的猜詞策略(Nagy 1997),但無法否認閱讀過程中的詞典使用是一種策略,而且“不能據(jù)此就斷定這是一種糟糕策略”(Scholfield 1997)?我們接受Hosenfeld(1977)的觀點,他說:“成功的閱讀者并非從來不查詞典……而只是在有效策略都失敗之后再查閱詞典?”
3)詞典與寫作
外語寫作牽涉到產(chǎn)出型詞匯策略研究?Harvey & Yuill(1997)做過一個實驗,指定學生在寫作中使用COBUILD詞典,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學生的寫作成績明顯提高?他們分析,該詞典中的“自然語言釋義”?“選自語料庫的例證”及“同義詞”可能發(fā)揮了作用?Laufer(1992)也實驗證明,詞典對于外語寫作確實有幫助,不過自撰例比自然例更有利于外語寫作?White & Arndt(1991)則研究建議,在寫作最后一稿時使用詞典可以解決某些詞匯問題?研究人員(Ervin 1979; Béjoint 1981; Katamine 1989)還研究發(fā)現(xiàn),學習者在寫作過程中普遍存在著詞典使用不足(under-use)問題,因而鼓勵充分利用詞典?另外,也有觀點認為詞典對外語寫作并沒有太大作用,因為現(xiàn)有詞典有著太多缺陷,例如沒有詳細?可用的語體?搭配及意義方面的信息(Nesi 1994),缺乏同義詞?語法等信息(Huang 1985)等?
4.5 詞典作為外語教學工具的特殊性
就教學過程而言,實際外語教學具有真實性與機動性,也能夠處理并滿足偶發(fā)性和復雜性情境?詞典囿于文本范式的制約,只能將其教學功能歸化在自身的語言自指性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中,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詞典也具有實際外語教學所無法比擬的特殊性?
第一,建構(gòu)有相對完善?系統(tǒng)的詞匯知識框架?Nation(1990)認為,如果外語學習者在詞匯使用方面要達到本族語者程度,應該掌握該詞八個方面的知識:1)口語形式;2)書寫形式;3)語法行為;4)搭配形式;5)使用頻率;6)所適用的文體;7)意義;8)語義聯(lián)想網(wǎng)絡?實際課堂詞匯教學或練習測試一般無法傳授并強化所有層面的知識,而現(xiàn)代詞典尤其是學習詞典通常都能滿足所有這些要求,其相對系統(tǒng)?成熟的詞匯知識框架有利于學習者詞匯能力的完善發(fā)展,也有助于他們心理詞匯的建立(桂詩春2006)?
第二,更有助于詞匯習得?從(有意)“注意”(noticing)與詞匯習得關(guān)系角度來說,對語言的某些特性進行有意識注意能夠讓這些特性凸現(xiàn)(salient)出來,有益于學習(Schmitt & McCarthy 1997)?詞典使用本質(zhì)上就是將注意力集中于語言特性的有意識行為(Scholfield 1997),因而有助于詞匯習得?從詞的形態(tài)理據(jù)與詞匯習得關(guān)系角度來說,前者對后者有著重要影響(黃遠振 2001)?形態(tài)理據(jù)涉及派生詞與復合詞,這正是現(xiàn)代詞典所著重處理的,因而不僅有助于學習者自動采用形態(tài)分析策略,認清詞素,準確推斷詞義,更有利于擴展詞匯習得的寬度與深度?從“賦值”(指一個外語形式被賦予相應的語義與語法價值)與詞匯習得關(guān)系角度來說,現(xiàn)代詞典可以利用到各種賦值條件,例如利用教學者的賦值條件(如吸納構(gòu)詞法知識),運用自行的賦值條件(如利用學得的構(gòu)詞法知識),還可以利用單一的賦值條件和多重賦值條件(如語音特征?形態(tài)特征與語義特征等),有助于學習者強化詞匯習得的深度?從詞匯直接指導與詞匯習得關(guān)系角度來說,研究者(Parry 1997)認為,對成年學習者來說,直接的詞匯指導不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須的,有利于拓展詞匯深度?詞典使用本質(zhì)上就是詞匯的直接指導或?qū)W習?
5.教學機制方法論:過程的模擬與復制
從詞典文本范式角度來說,詞典與外語教學的鏈接亦是一種本質(zhì)使然:詞典編纂者以社會(語言共同體)與個人之間的中間人身份向詞典使用者告知語言中語詞的多樣信息,從而完成一個教(教師)與學(學生)序列過程?加克(1981)對此進行了分析,他說:“從分析詞語形成,詞語對所描述的事物之間的關(guān)系的性質(zhì),詞語固有的敘述類型本身可以看出,詞典屬于教學論之列,因此它具有教育性作品的全部基本特征,不過,這種特征在詞典中具有其獨特的反映?”J. Dubois & C. Dubois(轉(zhuǎn)引自加克 1981)也指出,詞典與其他教學論著作比較,基本的相似點是說者?聽者與語言對象的獨特的相互關(guān)系?
外語教學是一門系統(tǒng)科學,有著自身的教學環(huán)境?教學對象和教學目標,也有著適合語言教學規(guī)律的教學方法,從而建構(gòu)出一套復雜?立體的教學機制?如果說傳統(tǒng)詞典文本所建構(gòu)的教學機制比較落后:信息簡單?功能單一?以教師(編纂者)為中心,這不但無法滿足詞典使用者的多樣化信息需求,也不利于他們的語言認知習得,有時甚至會不自覺地造成負面影響,那么,現(xiàn)代詞典則大膽引進并利用語言學?認知科學?教育學等理論,跳脫傳統(tǒng)詞典靜態(tài)的教學機制,極力張揚?突顯詞典教學功能,一方面積極模擬外語教學語境,另一方面極力復制外語教學機制,以期最佳地迎合外語教學規(guī)律,從而構(gòu)建意義并實現(xiàn)最優(yōu)的詞典教學效果?陳偉等(2007)對此已經(jīng)做了深入研究,我們這里不再贅述?
6.結(jié)束語
本文從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三個層面探究了詞典與外語教學對接界面的學理歸因?這里有兩點值得重點提示:
1)現(xiàn)代詞典順應應用語言學發(fā)展潮流而動,極度張揚教學功能而實現(xiàn)范式的時代演變,是兩者對接的關(guān)鍵條件?這其中,現(xiàn)代詞典迎合外語教學領域的質(zhì)變趨勢,實現(xiàn)了從“編纂者中心”向“使用者中心”的轉(zhuǎn)變,又顯得尤為重要?未來詞典應該根據(jù)認知科學和語言習得理論構(gòu)建范式,全面趨向教學的認知過程,趨向使用者的學習機制與認知策略,以提高他們的詞匯能力為旨歸,最終實現(xiàn)詞典范式從本性的教學功能向自顯的教學機制的轉(zhuǎn)變?
2)強調(diào)詞典范式教學功能的突顯,強化詞典與外語教學的鏈接,這迎合并切中了當前的后現(xiàn)代教育理念(陳偉2008)?充分發(fā)揮詞典的外語教學效能,本質(zhì)上就是強調(diào)建構(gòu)主義教學理念,突出外語學習的自主性與創(chuàng)造性?這有助于學習者更好地創(chuàng)造知識,有助于培養(yǎng)他們的社會意識?批判精神及終生學習意識,從而拓展他們的生存活力和持續(xù)發(fā)展的可能性?這是以知識創(chuàng)新和信息運用能力為主導的知識經(jīng)濟時代的要求,也是終生教育?回歸教育?繼續(xù)教育開始覆蓋個體生命全過程的要求?
參考文獻
[1] Ahmed, O. 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ies[A]. In Meara, P.(ed.). Beyond Words[C]. Virtual Library, 1989.
[2] Allen, V. F. Techniques in Teaching Vocabulary[M]. Oxford: OUP, 1983.
[3] Atkins, B.T.S. & Varantola, K. Monitoring dictionary u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 1997(1).
[4] Béjoint, H. The foreign students use of monolingual English dictionaries: A study of language needs and reference skills[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1(3).
[5] Bensoussan, M. et al. The effect of dictionary usage on EFL test performance[J].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1984(2).
[6] Bogaards, P. Dictionnaires pedagogiques et apprentissage du vocabulaire[J]. Cabiers de Lexicologie, 1991(59).
[7] Coady, J. & Huckin, T. (ed.).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 Rationale for Pedagogy[C]. New York: CUP, 1997.
[8] Cohen, A. D. Language Learning[M]. Boston: Heinle and Heinle Publisher, 1990.
[9] Ellis, N. C. Vocabulary acquisition: Word structure, collocation, word-class and meaning[A]. In Schmitt, N. & McCarthy, M. (eds.). Cambridge: CUP, 1997.
[10] Ervin, G.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by American students of Russian[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79(63).
[11] Grabe, W. & Stoller, F. L. Reading & vocabulary development in a second language: A case study[A]. In Coady, J. & Huckin, T. (ed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ress,1997.
[12] Halliday, M. A. K. Categories of the theory of grammar[A]. InKress, G. R.(eds.).Halliday: System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C].Oxford: OUP, 1961.
[13] Harley, B. Lexical Issues in Language Learning[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5.
[14] Hartmann, R. R.K. The bilingual learners dictionary and its user[J]. Multilingua, 1983(23).
[15] Harvey, K. & Yuill, D. A study of the use of a monolingual pedagogical dictionary by learners of English engaged in writing[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7(3).
[16] Hosenfeld, C.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reading strategies of successful and nonsuccessful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J]. System, 1977(5).
[17] Huang, G.F. The productive use of EFL dictionaries[J]. RELC Journal, 1985(2).
[18] Hulstijn, J. Retention of inferred and given word meanings: Experiments in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A]. In Arnaud, P. & Bejoint, H.(eds.).Vocabulary and Applied Linguistics[C].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19] Hulstijn, J. Mnemonic methods in foreign language vocabulary learning[A]. In Coady, J. & Huckin, T.(eds.).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C]. Cambridge: CUP, 1997.
[20] Iannucci, J.E. Subcategories in bilingual dictionaries[A]. In Lexicography as a Science and as an Art[C]. Kentucky: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1976.
[21] Katamine, L. A Comparison of the Adoption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of Native Arabic Learners[D]. University of Wales: MA dissertation, 1989.
[22] Krings, H. P. Was in den K塸fen von abersetzern vorgeht[A]. Eine empirische Untersuchung zur Struktur des abersetzungsprozesses an fortgeschrittenen Franz塻ischlernern[C]. Tübingen, Narr, 1986.
[23] Laufer, B. How much lexis is necessary for reading comprehension?[A]. In Arnaud, P. & Béjoint, H. (eds.).Vocabulary and Applied Linguistics[C]. London: Macmillan, 1992.
[24]Laufer, B. The development of passive and active vocabulary in a second language: Same or different?[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8(19).
[25] Lewis, M. The Lexical Approach[M]. Hove and London: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 1993.
[26] Li, L. Dictionaries and their users at Chinese universit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SP learners[A]. In McArthur and Kernerman(eds.)., 1998.
[27] Luppescu, S. & Day, R. Reading, dictionaries and vocabulary learning[J]. Language Learning, 1993,43(12).
[28] Nagy, W. On the role of context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learning[A]. In Schmitt, N. & McCarthy, M. (eds.)., 1997.
[29] Nagy, W., Herman, P. & Anderson, R. Learning words from context[J].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1985,20(2).
[30] Nation, I.S.P. Teaching and Learning Vocabulary[M]. Massachusetts: Newbury House, 1990.
[31] Nesi, H. The Use and Abuse of EFL Dictionaries[D]. University of Wale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1994.
[32] Nesi, H. & Meara, P. Patterns of misinterpretation in the productive use of EFL dictionary definition[J]. System, 1994(22).
[33]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Leiden: E. J. Brill, 1964.
[34] OMalley, J. & Chamot, A. (ed.). Learning Strat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 Cambridge: CUP, 1990.
[35] Padron, Y. & Waxman, H. The effects of ESL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cognitive strategies on reading achievement[J]. TESOL Quarterly, 1988(22).
[36] Parry, K. Building a vocabulary through academic reading[J]. TESOL Quarterly, 1991(25).
[37] Politzer, R. & McGroarty, M.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learning behavio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gains in linguistic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J]. TESOL Quarterly, 1985(19).
[38] Porte, G. Poor language learners and their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new vocabulary[J].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1988(42).
[39] Pressley, M. et al. The mnemonic keyword method[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82(52).
[40] Schmitt, N. & McCarthy, M. Vocabulary: Description, Acquisition and Pedagogy[M]. Cambridge: CUP, 1997.
[41] Scholfield, P. Dictionary use in recep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 1997(12).
[42] Stahl, S.A. & Fairbanks, M.M. The effects of vocabulary instruction: A model-based meta-analysis[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86(56).
[43] Summers, D. The role of dictionaries in language learning[A]. In Carter, R. & McCarthy, M. (ed.).Vocabulary and Language Teaching[C]. New York: Longman, 1998.
[44] Tomaszczyk, J. Dictionaries: Users and uses[J]. Glottodidactica, 1979(2).
[45] Tono, Y. Can a dictionary help one read better?[A]. In Lexicographers and Their Works[C].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89.
[46] White, R. & Arndt, V. Process Writing[M]. London: Longman, 1991.
[47] Widdowson, H. The changing role and nature of ELT[J]. ELT Journal, 1992(4).
[48] Wilkins 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2.
[49] Zimmerman, C.B. Do reading and interactive vocabulary instruction make a difference: An empirical study[J]. TESOL Quarterly, 1997(31).
[50] 陳 偉. 詞典課程開設的后現(xiàn)代教育理念解讀[J]. 辭書研究, 2008(6).
[51] 陳 偉,等. 教學功能突顯與詞典范式演變[J]. 外語界, 2007(6): 35-44.
[52] 董燕萍. 交際法教學中詞匯的直接學習和間接學習[J]. 外語教學與研究, 2001(5): 186-192.
[53] 桂詩春. 外語教學的認知基礎[J]. 外語教學與研究, 2005(4): 243-249.
[54] 桂詩春. 英語詞匯學習面面觀——答客問[J]. 外語界, 2006(1): 57-65.
[55] 黃建華,等. 雙語詞典學導論[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1.
[56] 黃遠振. 詞的形態(tài)理據(jù)與詞匯習得的相關(guān)性[J]. 外語教學與研究, 2001(6).
[57] 加 克. 詞典學發(fā)展的某些規(guī)律性[A]. 石肆壬(選編). 詞典學論文選譯[C].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1.
[58] 杰尼索夫. 語言學描寫的幾個理論問題[A]. 石肆壬(選編). 詞典學論文選譯[C].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1.
[59] 卡西爾. 人論[M].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5.
[60] 吳 霞,等. 非英語專業(yè)本科學生詞匯學習策略[J]. 外語教學與研究, 1998(1).
[61] 徐海銘,等. 語義習得模式及其哲學意蘊[J]. 外語研究, 2005(5): 10-16.
[62] 雍和明. 交際詞典學[M].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3.
[63] 趙彥春. 認知詞典學探索[M].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3.
基金項目: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chuàng)新項目資助,項目編號為:08YS123?
作者簡介:陳偉,上海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現(xiàn)在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理論詞典學?教育科學?翻譯學?
收稿日期 2008-03-06
責任編校 采 玉